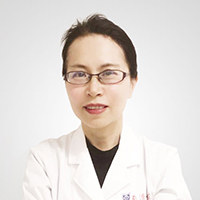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严海

我时常会想起赛达特的夜空,那如同一帘巨大的黑幕,缀满了闪烁的繁星,晚风中送来阵阵清真寺宣礼塔的诵经,伴随着淳朴的民风,回荡在北非小城的上空……
2009-2011年,作为中国援助摩洛哥医疗队成员,我曾在那里工作,两年援外的经历,充满了刻骨铭心的回忆。
我们去服务的是塞达特省的哈桑二世国王医院,相当于我们的省人民医院,是一家服务于当地一百多万人口的公立医院。尽管在出发前国内的法语培训中,我们已经对摩洛哥的医疗发展水平有所耳闻,但当我们真切的踏上这片土地,面对的现状还是让我们感到震惊。
医院里最高的建筑就是日本援建的妇产科中心,也就一栋三层的小楼。在医院的院子里,羊儿三三两两在吃草。来到手术室,房间里只有一台上海医疗设备厂的MHJ-Ⅲ B型麻醉机。我正打算琢磨下这台比我年龄小不了几岁的老古董如何开机,竟然一只猫从下面钻出来,伸个懒腰,悠闲地在手术室里踱步而去……
我们中国医疗队都是在摩洛哥的公立医院工作的,所服务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贫苦百姓。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连法语也不会讲,过来看病都要通过当地护士帮我们把阿拉伯语或柏柏尔语翻译成法语,我们才能大致问清病史。
受到长期宗教、文化和教育的熏陶,这里的患者都很尊重医生,确切地说是整个社会都很尊重医生,而中国医生则更受尊重。仅塞达特一地,从1976年开始的中国援摩医疗队就薪火相承,这里25%以上的孩子是中国医生免费接生的,更不要说接受其它医疗帮助的患者。而像这样的中国医疗队有十二支之多,一百多名上海医生分散在摩洛哥的穷乡避壤工作。摩洛哥的民众提到中国医生,都常常自豪地地帮你说起他的哪个亲戚得到过中国医生的帮助。
交接工作转眼结束,我们医疗队随即开始正式上班。我们国内培养出来的医生,适应团队作战模式。碰到疑难杂症,往往逐级汇报请示,上级医生也责任在肩,接到求助要求后后也必须给与支援。但是在国外,他们的工作模式就是单兵作战,我们自己也没有上级医生,这使得我们只能适应他们的工作习惯。而我是在手术室内工作,还不能带翻译进去。在那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每天我都硬着头皮靠自己那点日常法语会话,加上英语的专业词汇,揣着一只电子词典,辅以肢体语言比划,在手术室独自打拼。我不光要完成自己的手术,还要带领一帮当地的麻醉护士团队,维持手术室的日常运转。
不过幸运的是,一周下来,新环境适应得还算顺利,法语也能开始与他们简单沟通,医疗救治工作顺利开展。摩洛哥患者来手术室,常常都是光脚,自己走进来。冬天时手术室空调也不足,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抱起走廊上瑟瑟发抖的孩子进手术室开刀。在这里做医生,我们就是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能够激发出我们内心最大的善良,促使我由衷地想对这些朴实的患者好一些,再更好一些。
工作刚熟悉没多久,我们就赶上一次印象最深的大抢救。那天是八月的一个周末傍晚,我和外科医生邹建华值班。刚从厨房晚饭归来,迎面碰到两个护士,“DOCTOR! VITE! VITE!”( 快!快!)。他两焦急地比划着指向急诊。“ANESTHESISTE! CHIRURGIEN! URGENCE!”(麻醉医生,外科医生,急诊!),我们立即奔向急诊。
来到急诊,门口已经停了一辆救护车,闪着警灯,旁边还停着好几辆警车。一大群人围在门口,传出阵阵哀号。几名警察维持着秩序,看到我们奔来,人群立即闪开一条通道。
担架车上躺着一名中年男子,面色惨白,呼吸急促,但体表无开放性创口。
急诊科医生跟我们简单交代了病情:两小时前,在马拉喀什到卡萨布兰卡的高速上发生一起车祸,同车三人,都送往临近医院,轻伤的两人已经处理,这位重伤者怀疑胸腹部联合伤,当地医院没法处理,本想转送卡萨布兰卡,结果救护车开到半路,发现伤者呼吸衰竭,就赶紧转送送来我们这了。
我马上组织护士一面开放大静脉,一面连接监护。一量血压,才70/40mmHg,心率140-150次/分,末梢氧饱和度96%。我们马上开始输液,备血,通知实验室尽快完成术前检查。
邹建华主任马上给伤者做了个腹穿,抽出一针筒不凝血。做B超看来是来不及了,邹主任判断是腹腔内大出血,立即通知手术室准备剖腹探查。我也马上通知血库做好配型、备血准备,同时叮嘱急诊间护士一面快速补充胶体,维持血容量,一面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并立即去手术室准备麻醉所需的设备和药品。
半小时后,伤者已经躺在手术台上,血库电话也来了,B型备血可用1000ml,患者血压已经升到105/60mmHg,准备开始麻醉。
就在插管前,我习惯性的拿听诊器一听,不对,患者的左侧呼吸音很低,叩诊也都是鼓音。急请放射科技师用手术室的X光机台上摄片,发现是左侧胸腔血气胸,多发肋骨骨折,左肺压缩50%,回头再看末梢氧饱和度,只有88%了。
我一面给伤者扣上氧气面罩,一面通知护士马上叫胸外科,准备放置胸管。
回复很快来了,胸外科医生斋月休年假了。怎么办?
邹建华医生无惧地说:“我以前做过胸外科,来吧,严海,你帮我当助手。”
他拿过器械,熟练地划皮、穿刺,我忙着帮他打局麻、置管、固定缝线,旁边两个护士看得十分惊喜“BIEN! (好棒!)”。
水封瓶一接,胸腔闭式引流开始工作,被压瘪的肺开始张开,末梢氧饱和度很快回到了99%。
“开始麻醉插管!”我向麻醉护士下达指令。五分钟后麻醉完成,开始手术。
手术开始,腹腔一打开,大量的血液涌了出来,摩方的洗手护士立刻紧张地拿着吸引器忙碌着。
我一面密切关注监护仪上的参数,一面密切与台上的邹医生交流着手术情况。
时针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吸引瓶里的积血已有1800ml,并且越来越多,病人的心率也越来越快,血压也越来越难维持,收缩压一度掉到40mmHg以下。医院里仅有的1000ml的B型血也已输完。如果再要拿血,要到八十公里外的卡萨布兰卡市血站去调用。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按照当地的做法,竟然是让患者家属自己设法去另一座城市取血。我觉得今天这个病人这关要难过了。这时,血库给我电话,说血库还有O型血,以前法国医生抢救病人时用过。
“异型输血!”,这以前只在书本上读到过,但是在我学医以来,所有接触过的国内医院没有人以用过这个“古老方法”。
确切地说, O型血是“危险的万能血”。O型血的红细胞上没有A、B抗原,所以把O型血的红细胞输给A、B、AB血型患者时,可以临时救急。但是摩洛哥受到血液分离技术水平限制,他们的红细胞血袋里含有少量血浆的,而O型血的血浆中是含有抗A、抗B抗体,一旦把O型血的血浆输入其它血型患者体内,就可能发生凝集反应,使受血者红细胞遭到严重破坏而导致溶血,这可是同样危及生命的。
台上的邹主任行医三十年,算的老法师了,他表示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不输血这个患者眼看就要撑不住了,我们陷入了两难,都难以预料。
事已至此,我只有和家属又谈了一次话,主要强调目前的大失血抢救困境和异型输血的可能严重后果。家属啥也没说,一个劲地感谢我们中国医生的努力,同时表示即便患者死亡,也只是回归真主。
有了家属的无条件信任,我决心冒险一搏。开始输注O型血。我旁边准备好各类抗过敏和抢救药物,还好一切顺利,没有出现可怕的情况。一个小时过去了,手术结束,没有出现严重的输血反应。感谢真主!
术毕统计:伤者粉碎性脾破裂,左肋多发性骨折,行脾切除术,术中出血达2200ml,输B型血1000ml,O型血500 ml。
邹医生和我一起把患者送进了监护室,与监护室医生交班完毕后,我们俩总算松了口气。
由于处理得当,术后三天,患者出了监护室,回当地医院休养。
伤者及家属非常感激,感激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也真心的感谢这份信任,正因为这份信任,我们可以放下顾忌,一心的围绕病人处理,甚至采取“超越执业范围处理”,冒险“超禁忌输血”来抢救生命。
反观我们国内,确实医疗资源和技术比那里高出一截,但是医患之间的信任正好相反,医院的被迫制定各项规定流程,把医生的执业行为控制的非常严格。
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保护了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主张,但是也限制和监督了医疗的整个流程,产生了一定内耗。以至于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每一例患者治疗过程中的详细的文书、谈话、签字,我花了好些力气才适应回来。
十四年过去了,虽然这只是我们繁忙工作中的一例普通抢救,我们所做的也只是出于医生的本能,但无论何时回忆起来,我们感到深深的幸福——一种无条件被患者信任的幸福。
可能也就是这股动力,激发出每一个援摩医生尽全力去帮助这些淳朴的人民;也正是这股动力,中摩人民将心换心,使得几十年来中国援摩医疗结出了的丰硕成果。
(通讯员 顾海鹰)
 39健康网
39健康网 会议通知|第25届心律学大会(CHRS 2025)将在郑州举行2025-01-23
会议通知|第25届心律学大会(CHRS 2025)将在郑州举行2025-01-23 回望长安,CCHIO六万参众还余音绕梁2024-11-25
回望长安,CCHIO六万参众还余音绕梁2024-11-25 肺结节就是肺癌前兆?支修益称,肺结节存在过度诊断、过度治疗2024-11-24
肺结节就是肺癌前兆?支修益称,肺结节存在过度诊断、过度治疗2024-11-24 肿瘤防治 赢在整合—2024中国整合肿瘤学大会精彩收官2024-11-23
肿瘤防治 赢在整合—2024中国整合肿瘤学大会精彩收官2024-11-23 2024 CCHIO重磅发布|医患互动小程序CACA专家平台正式上线2024-11-22
2024 CCHIO重磅发布|医患互动小程序CACA专家平台正式上线2024-11-22 樊代明院士:肿瘤防治再上台阶,要用好AI 也要有高水平医生2024-11-22
樊代明院士:肿瘤防治再上台阶,要用好AI 也要有高水平医生2024-11-22 【2024 CCHIO】中外院士齐聚西安,深度探讨肿瘤精准医疗与未来趋势2024-11-21
【2024 CCHIO】中外院士齐聚西安,深度探讨肿瘤精准医疗与未来趋势2024-11-21 七成肝癌确诊已是中晚期!樊嘉院士:肝癌治疗要更加个性化、精准化2024-11-21
七成肝癌确诊已是中晚期!樊嘉院士:肝癌治疗要更加个性化、精准化2024-11-21 郑州治结直肠癌正规医院推荐2025-01-24
郑州治结直肠癌正规医院推荐2025-01-24 资阳治结直肠癌医院推荐2025-01-24
资阳治结直肠癌医院推荐2025-01-24 襄阳哪家医院治前列腺癌比较专业2025-01-24
襄阳哪家医院治前列腺癌比较专业2025-01-24
 自卑心理评估,测你内心真实的自卑程度心理测试
自卑心理评估,测你内心真实的自卑程度心理测试 你是什么级别的剁手党?心理测试
你是什么级别的剁手党?心理测试 皮肤容易过敏是特禀体质吗?心理测试
皮肤容易过敏是特禀体质吗?心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