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监局成立十年以来,对于药品流通占70%以上、药品使用中最重要的环节——医院,却始终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很难监管到医院,药监局一度被业内人士戏称为“药店局”。
“我以我十年的经历证明,医药分家其实分掉的是卫生和药监等主管部门的责任,带来的是不受约束的权力。”
一起十年前的改革,似乎又要“从头再来”。1998年,原卫生部药政局分出,与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合并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从而开启中国在卫生与药品(医械)监管层面的“医、药分家”时代。十年后,在数起医院内药品不良事件和郑筱萸腐败案之后,国家药监局再次回归卫生部。医药十年分合,经历风雨无数,折射出中国医药监督体制的难言之痛。
升部遇阻
尽管坊间早有流传,但并入卫生部的消息确认后,对于不少药监人而言仍显突然。
3月11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作了说明,指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理顺食品药品监管体制。
2006年以来,尽管出了郑筱萸(原国家药监局局长)案,但国务院有关领导仍多次强调食品药品工作的重要性,并总体肯定药监系统这些年的工作。而药监局去年也在积极“刮骨疗毒”,出台多项廉政措施,不遗余力肃清郑筱萸案影响。
实际上,在郑案审理期间,国家药监局机关还在积极酝酿搬家事宜,据说连各司的办公室也已安排好。新地址是位于西便门的原国家烟草局大楼,办公面积有三万平方米,比国家药监局现在大楼大了一半以上。有心人士分析,这或意味着国家药监局将升格为正部,与卫生部平级。
国家药监局自1998年成立以后,“升部”就一直是局长郑筱萸的一大目标。2003年将食品部分监管职能并进,更名为现在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更是强劲昭示出郑筱萸的“升部愿望”。
然而,大部制方案证明,这只是药监人的一个愿望。
事实上,在华建敏正式宣布前五天,列席全国人大开幕式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邵明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赞同药监局合并入卫生部的卫生大部制改革设想。
一位有心人士注意到,早在去年12月26日,新华社就曾报道,卫生部部长陈竺就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加强食品药品监管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而按我国医药管理体制,2001年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以后,药品便由国家药监局专管,相关汇报理应由位列国务院直属局的药监局新局长邵明立来作。“回头看来,这或许是药监局并入卫生部的最早信号。”该人士说。
由卫生部管理之后,国家药监局将与同样由卫生部管理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地位平等。按“部管局”有关规定,国家局在工作中需要请示国务院时,应由卫生部向国务院呈文。有药监人士认为,“药监部门地位的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分久必合?
南开大学宋华琳博士近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药品监督制度。不过,他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明白,十年前成立国家药监局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
流行的说法是,成立国家药监局是为了学习美国FDA,突出药监部门的独立性,加强对药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然而十年后,当药监局改由卫生部管理后,学习美国却成为相反的理由——FDA并非完全独立,它实位于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之下。
宋华琳介绍,1998年前,中国药品监管一直存有两个体系,一是原卫生部下属的药政局(处),一个是归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及各地方局)。前者主要负责药品审批和医院用药的监管,后者则主要管理企业生产经营。前者与医院关系密切,后者则被视为企业利益的代言人。“两个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存在”。
一位原医药系统人士对此予以证实。他透露,卫生与医药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注册审批上。1998年之前,药品的审批权在卫生部药政局手中,地方各卫生厅局也有一定的审批权。企业如果研发生产新药,通常是先将材料报给原医药局,再由后者报给卫生部(厅)。两个婆婆同时存在,医药企业为此叫苦连天。
“当时的情况是,卫生部门想越过医药局直接给企业批药,医药部门则想把审批权从卫生部药政局那拿过来。两个部门天天打架。”
国家药监局成立之前,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当时国内药品领域已经是乱象丛生,路边一个平房内就可生产药品,药品的购销更像是菜市场批发。为此国务院办公厅曾于1994年和1996年发文整顿。当时医院的市场化改革也在加快,在“回扣”风的刺激下,假药劣药也开始进入医院,医院的安全用药形势日益严峻。由于卫生部门与医院的“父子”关系,靠其属下的药政部门监管已越发显得力不从心。
香港中文大学刘鹏的博士论文题目即为“中国药监史”。在他看来,当年药监局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药品管理过程中,卫生和医药两个部门都感觉到因为体制不顺的诸多问题,都想借FDA模式将管理权统揽到自己手中。
医药博弈
新成立的国家药监局,由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局长郑筱萸任局长,原卫生部药政局局长邵明立则成为第一副局长,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卫生部管理)副局长任德全亦任副局长。办公地址则为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大楼。
就结果而言,原国家医药局似乎主导了这次中国药监史上的最大变革。据一位药监系统资深人士回忆,事实上当年成立国家药监局时,最为积极的也是原医药管理总局。“郑筱萸为此做了很多工作,请了很多人出国考察。”一位知情人士说。
在新成立的国家药监局120个编制中,原国家医药总局占了80个,原卫生部药政局有30多个,另有不到10人来自原中医药管理局。“各方对此似乎都不满意。医药局尽管占了大部分编制,却因为原医药局有100人分流而不满;原卫生部药政局尽管大部分人都过来了,却觉得自己是外来人;中医药局的人则认为自己完全被边缘化。”上述人士说,“现在看来,当年药监局一成立就面临先天不足,原来就有矛盾的人撮合在一起,工作难开展。”
新药监系统似乎“生不逢时”——1998年恰逢新中国成立以来动作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各部门纷纷裁人,为减轻分流压力,均对新成立的药监编制虎视眈眈。“有的地方上,药监局长是由地方领导的秘书甚至司机担任,根本不懂药。”
据悉,在新的药监系统中,省以下采取垂直管理模式,而主导者同样是各省原医药局。来自卫生系统的王力(化名)曾担任黑龙江省某县药监局副局长。据他介绍,当时不少县的医药局已经改革,变成了医药公司。结果因为要成立药监局,原来职工们“一步登天”,成了公务员。“甚至一些下岗多年的人也进了药监局”。
然而随着郑筱萸案的发生,形势则发生了根本变化。事实上,据国家药监局一位资深人士透露,郑筱萸案能够顺利查处,与国家药监局内原卫生系统干部的举报揭发密不可分。
郑本人落马后,全国药监系统开始整顿,不少卫生系统的干部被充实进来。以国家局为例,药品司司长、器械司司长、新闻发言人等多数重要岗位均来自卫生系统。办公室8名司级(含副司级)干部中,据说有6人来自于卫生部。省级地方局也是一样,据知情人士透露,郑筱萸案发生之后,不少地方药监局局长被调整,现在原医药局出身的局长已经寥寥无几。
管不了医院
国家药监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医药分家”时代的开启。自此之后,卫生部专管医院和医生,药监局则负责药品和医疗器械。中国的药品和医械的监管,第一次从体制层面脱离卫生系统。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体制亦深深影响到中国的医改进程。
据称,药监局成立之初,时任总理朱镕基曾将新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叫到一起,对张文康说,“医出了问题我拿你是问”,然后又对郑筱萸说,“药出了问题我拿你是问”。
结果五年之后,张文康因为SARS瞒报问题去职;八年之后,郑筱萸腐败案案发,其本人被判死刑,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判死刑的国务院直属部门首脑。
尽管随着国家药监局的成立,“医”和“药”从体制上实现了分家。但不争的事实是,这种分家从一开始就不彻底。
这一点在“医院制剂”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所谓医院制剂,是指市场上没有的、由医院研发、生产流通的一种特殊药品,只允许在本医院使用,不能上市流通。药监局成立后,医院制剂面临一个异常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它是药品,理应由药监管;另一方面,它在医院内研发、生产、使用,不进入市场,又似属卫生管。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药监局成立伊始,曾打算将医院制剂的监管权纳入。不过在当时卫生部主要领导的极力争取下,国务院主管领导最终同意保留医院制剂,并交由卫生和药监一起管。这使得我国2001年颁布实施的药品法中,专门就医院制剂设一章节,以区别于国字号药品。
按药品法规定,医院制剂由省级卫生部门审核,由药监部门批准。即“审的不批,批的不审”。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实际操作中,以卫生部门的审核为主,药监部的批准多为形式。然而问题是,医药分家之后,由于卫生部曾有的药政职能被并到药监局,卫生部门事实上已经没有药品方面的监管岗位和专职人员。
很少有人知道,近年来我国除了由国家药监局审批的数万种国字号新药之外,另外还诞生了数万种由地方卫生和药监部门共同审批的医院制剂,由于医院制剂的价格制定缺乏市场参考,价格大都不菲,成为医院隐性利润的重要来源。
“国家药监总局成立十年来,其实并没能完全把药全管起来。”国家药监局一位资深人士说。
审批乱象
国家药监局成立后,药品审批权成为其权力和利益的源头。企业生产一种新药需向其交纳数万元的审批费。在郑筱萸当政期间,这项事关国家生命安全的权力近乎滥用。
据一位国家药监局内部人士透露,药品的审批一度出现这种情况:某企业的申请资料刚刚交上,马上被国家局的人复印多份高价卖给其他企业,然后再等到其他企业递交类似的申请资料后一起批准。有的企业要想拿到批文,竟需到国家药监局个别领导家中去取。
审批乱象却并非始于郑筱萸。国家药监局成立之前,除了卫生部药政局可以批药,各省级卫生厅(局)也有审批权。由于标准不一,即便是同一种药品,在质量上也相差很大。药品审批的各自为政现象,成为当时医药界的最大弊病。
为了统一标准,国家药监局将审批权统一上收,结束了药品审批乱象,这便是着名的“地标转国标”。据悉,当时需要重新审批的药品多达15万种。其中有不少是卫生药政部门赶在药监局成立前“抓紧”审批的。
由于换发文号工作量太大,郑筱萸曾签发了187号和582号两个文件,降低药品审核标准。文件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语句:企业申报时提供的有关材料可为复印件,由省级药监部门重点审核其原生产批件和原始档案,专项小组仅对上报的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并对原始档案进行抽查核对。“一句‘形式审核’,让国家药监局的法定监督职责也变成了‘形式’。”
在将药品审批权上收之后,地方药监局的权力和利益大为缩水。不知是否为了“安抚”,国家局允许省级药监局审批三类以下的医疗器械。这使得医疗器械的监管比药品更为薄弱。有药品厂家看准这一机会,把原本在国家药监局难以注册的新药在地方省局以医疗器械的形式注册。
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十年来促使有关部门取缔9种问题医疗器械,正是处在这一背景之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昂贵的、经过合法注册的医械产品,有的甚至是在家庭作坊中生产。
陈晓兰后来知道,医疗器械领域最重要的一部法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是国家药监局成立后在短短七天内制定的,其主要起草者,正是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2006年药监反腐风暴中第一个落马者。而这部法规的出台,意味着产品质量法对医疗器械已经起不到约束作用。相应地,质监部门也退出了医疗器械的监管。
一药两制
3月8日,中国食品药品监督信息网上,出现一篇题为“市场化路线大败局”的热帖,作者“种瓜得豆”疑为药监内部人士。在他看来,医药合并意味着我国的药品市场化路线的失败。
这篇文章分析:在权力划分上,药监过小而卫生过大,药监对药品质量安全控制的权利不完整不充分,对卫生部门不具破坏力和推动力,对卫生体制发挥不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尽管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药品的研制、审批、生产、经营、使用进行全面监督。可由于历史原因,国家药监局成立十年以来,对于药品流通占70%以上、药品使用中最重要的环节——医院,却始终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很难监管到医院,药监局一度被业内人士戏称为“药店局”。
陈晓兰举报的所有问题都发生在医院里,她发现药监部门对药品和医疗器械使用的监管只能到“说明书”为止。“进了医院之后怎么用,药监(部门)说是医院的事,他们不管。”
卫生部门似乎也乐得配合。比如《上海市医疗机构管理办法》中有这样一条:公安、工商、规划、计划、物价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卫生行政部门做好医疗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细心人可以发现,最重要的部门药监恰恰漏掉了。
“药监部门不敢进,卫生部门既没人懂又无法定执法权。医院成了假药和假医疗器械的安全港。”陈晓兰说。
国家药监局近年在压力下发出多个医疗器械的相关文件,不过并没有起到作用——它们只能通过药监部门发到企业里,却到不了医院。以“氦氖激光血管内治疗仪”为例,国家药监局早在2004年5月就发了文。可是该产品在医院真正停止使用,却是在2005年3月16日卫生部发出整顿“血疗”的紧急通知之后。
L是某市药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在他看来,药品的监管应该比做一条河流,理论上应该是全程监管。可是我国现状是,药监部门只能管到30%上游和中游,占70%的下游管不了,但要承担全流域的责任。“综观药监十年,对药监部门的动作卫生部门我自岿然不动。药监处处受制于卫生,最终不断收缩战线,埋头于药品生产和药品零售领域,基本无法有效介入医疗机构环节的药品监管。”“种瓜得豆”在帖子中写道。
监管悖论
2006年发生的齐二药(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三院十多位患者使用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公司的假药而死亡)事件,让药监系统的公信力深受打击,亦被认为是郑筱萸落马的一大原因。然而L处长却透露,对于药监系统而言,齐二药事件的结果让人哭笑不得:事件发生时,国家药监局刚建立起药品不良反应上报制度,要求医院在发生不良反应时上报药监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成立多年的药监第一次真正介入医疗机构的监管。而齐二药事件也正是国家药监局率先对外披露。“本来药监局是用来向中央请功的。”L说,“没想到经过媒体放大,舆论反而将矛头对准了药监局。”
L处长认为,药监系统从一成立时起,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悖论:查处问题同时也是暴露问题的过程,工作做得越多越扎实,问题暴露得也越多越明显。
就在各种药品不良事件让药监系统深感被动之际,刚刚经历了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的卫生系统却全身而退。
在齐二药问题上,卫生系统普遍认为医院不应该承担责任。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为中山大学附属三院鸣冤。认为医院按规定通报了药品不良反应,如果为此承担相关责任,那么势必会对这一制度造成影响。“负责任的医院不应承担不负责任的企业的责任”。
然而一位药监人士对此质疑:“齐二药之事,除了查药厂造假,怎么就没人查一查,假药是如何流进医院的?”中山三院用的药无疑都是通过药品招标进入的,而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药品招标制度,一直都是由卫生部门操办。
药监系统成立之后,医院用药安全便面临新的考验。据陈晓兰介绍,以前医院里有一个重要岗位:临床药师。他们是负责医生用药的专业人员,不仅懂医学和药学,还非常熟悉药物的剂量、配伍以及相互作用。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医生处方的合理用药和安全用药。
临床药师除了可以在用药安全上把关,还可以监督医生乱开回扣药现象。“医药分家以前,临床药师时常会把医生们开出有问题的处方退回去,对医生而言这也是颇没脸面的事情。”陈晓兰说。
然而药监局成立后,医院开始执行由卫生部门制定的执业医师制度,而药店开始实施药监部门制定的执业药师制度。夹在中间的临床药师却在医院失去了位置。“这给用药安全和诊疗安全埋下了极大隐患。”陈晓兰说,“现在药房往往积极配合医生多开药,以前屡见不鲜的因违规用药而退处方的情况没有了。”
与此同时,发生医院里的不良事件则渐渐上升,并成为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的重要导火索。“许多病人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医院,死了之后还没法打官司,因为最后往往找不到一个责任人。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医闹’。”
来自卫生部的数字表明,全国由于医患纠纷引发的冲击医院等恶性事件,2002年有五千多起,2004年上升到八千多起,2006年则将近一万起。“十年来,我反映的所有问题,都发生在医疗机构内,都与医疗服务安全直接有关。我以我十年的经历证明,医、药分家其实分掉的是卫生和药监等主管部门的责任,带来的是不受约束的权力。”陈晓兰说。
(责任编辑:黄彬)
 39健康网
39健康网 全球首例!试管婴儿技术成功阻断环状染色体,他们终于生下健康宝宝2024-03-20
全球首例!试管婴儿技术成功阻断环状染色体,他们终于生下健康宝宝2024-03-20 周宏伟:用检验医学打造健康新标靶2023-08-24
周宏伟:用检验医学打造健康新标靶2023-08-24 一胖毁所有?不,被你嫌弃多年的脂肪,其实好处不少2023-01-30
一胖毁所有?不,被你嫌弃多年的脂肪,其实好处不少2023-01-3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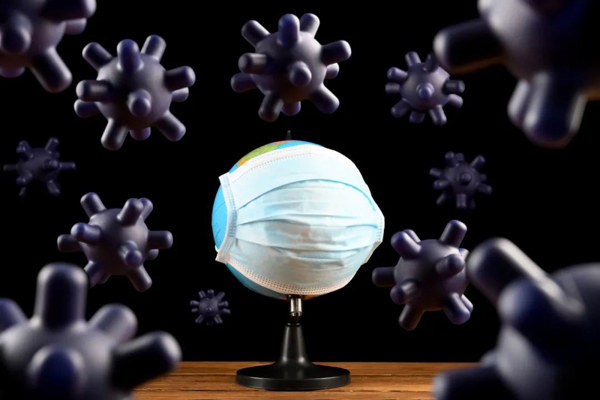 钟南山张文宏最新研判 :疫情高峰可能在一个月内杀到2022-12-15
钟南山张文宏最新研判 :疫情高峰可能在一个月内杀到2022-12-15 市场监管总局发文:核查哄抬连花清瘟药品价格,已提取多平台数据2022-12-09
市场监管总局发文:核查哄抬连花清瘟药品价格,已提取多平台数据2022-12-0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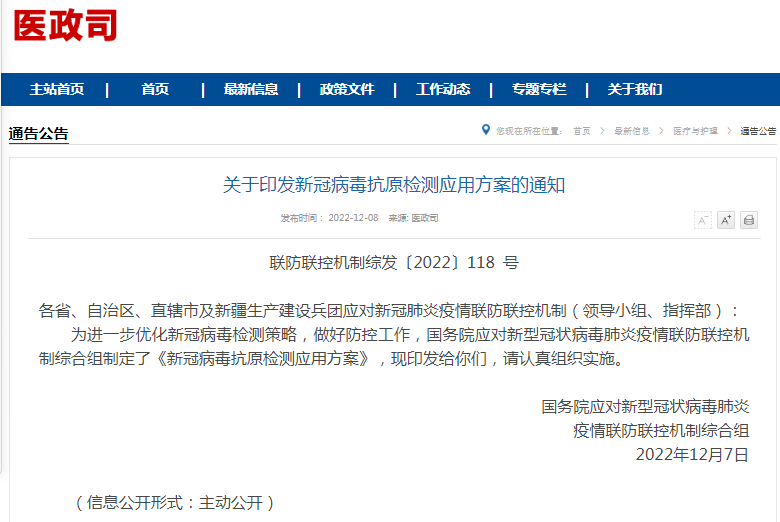 自测阳性向谁报告?老年人群如何检测?国家权威发文2022-12-09
自测阳性向谁报告?老年人群如何检测?国家权威发文2022-12-0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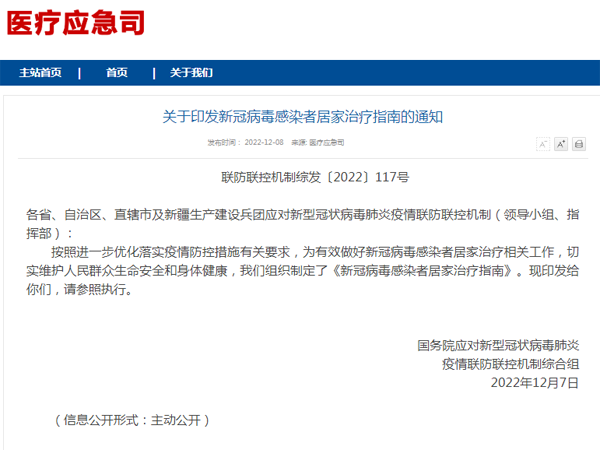 附常用药参考表!国家发布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2022-12-08
附常用药参考表!国家发布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2022-12-08 中国万人研究:8大负面情绪堪称“催老剂”,比抽烟还伤身2022-11-04
中国万人研究:8大负面情绪堪称“催老剂”,比抽烟还伤身2022-11-04 B超可以检查肾脏问题吗2024-05-02
B超可以检查肾脏问题吗2024-05-02 16岁男生肾虚的表现2024-05-02
16岁男生肾虚的表现2024-05-02 IgA肾病治疗2024-05-02
IgA肾病治疗2024-05-02
 自卑心理评估,测你内心真实的自卑程度心理测试
自卑心理评估,测你内心真实的自卑程度心理测试 你是什么级别的剁手党?心理测试
你是什么级别的剁手党?心理测试 皮肤容易过敏是特禀体质吗?心理测试
皮肤容易过敏是特禀体质吗?心理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