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从业11年、接生过1000多名婴儿的妇产科医生,罗军恐怕很难想到,自己会因为救活一个孩子而挨打。
而向他“挥出一拳,又踢了一脚”的打人者,恰恰是这个孩子的父亲。2011年11月8日,当陈立得知自己曾经要求放弃治疗却被罗军抢救成活的孩子,经检查患有“缺氧缺血性脑病”时,他愤怒地冲向罗军的办公室。
“我说过不要孩子,为什么还给救回来!我要和一个傻瓜过一辈子了!”这个父亲喊道。
救死扶伤的罗军也被惹火了:“你这个父亲可以不要小孩,我这个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这一幕被一家媒体曝光后,迅速引发了热议:有人指责大夫的好心反倒害了孩子以及家庭,还有人坚持“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看来,救还是不救,不仅仅是哈姆雷特遭遇的难题。
当看到刚刚出生的婴儿拼命地吸气时,罗军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救活他”;“脑瘫”这个医学术语吓坏了陈立,他萌生了放弃孩子的想法
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陈立和王静已经为迎接孩子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早在3个月前,他们就在商场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婴儿床。
噩运的到来没有任何先兆。2011年11月3日凌晨4点多,剧烈腹痛的王静被丈夫陈立送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经过初步诊断后,值班医生罗军立刻发现了眼前的危险:胎儿有窒息情况,必须尽快送入手术室。
陈立回忆,当时医生告诉自己,孩子即使生下来,“也是个大白痴”。但罗军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他声称自己只是按照惯例将“最坏的情况”告诉家长,“可能会白痴、脑瘫甚至死亡。”
无论如何,“脑瘫”这个医学术语还是吓坏了陈立。尽管萌生了放弃孩子的想法,他还是签下了手术同意书。
始终被疼痛折磨的妻子并不太清楚这一切。“我疼得太厉害,只是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说话。”王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30多分钟后,她顺产了一个4斤半重的婴儿。
这对父母没有想到,这只是噩梦的开始。罗军发现新生儿的健康状态评估(阿氏评分)仅为2分,而3分以下即属重度窒息。
他一边让护士向家长通报情况,一边坚持插管抢救。3分钟后,婴儿的呼吸和心跳都恢复了正常,阿氏评分达到6分,基本正常。可穿过几道安检去通知陈立的护士带回了令人意外的消息,“家长说,孩子不要了。”
如今,这对夫妇已经不愿回忆当时为什么作出“不抢救”的决定。可在很多人看来,理由显而易见,“抚养脑瘫患儿对整个家庭是一场灾难”。
一则新闻或可为此提供例证。1998年,广东东莞的一对白领夫妇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一年后,这对早产的儿子被确诊为脑瘫。本来生活悠闲的母亲不得不承受重担,她带着孩子去各地寻医,亲手为他们熬制中药。她辞去了工作,每天抱着他们洗澡、喂饭,直到13年后。
这个迅速衰老的母亲曾经自信地告诉亲戚,“我坚信我的儿子可以走路出现在你们面前。”但毅力和决心并没有使病情发生任何改变,十几年后,她的孩子们依然大小便不能自理,甚至不能正常行走。
“我越来越老,两个儿子越来越重,我已经抱不动他们,如果我和丈夫不在了,他们怎么办?”最后,这个母亲在浴缸里溺死了双胞胎儿子。
可在手术台上,医生罗军来不及考虑这些,当看到刚刚出生的婴儿拼命地吸气时,他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救活他”。
然而,这个出于医生职业本能的决定却被很多人质疑。有人质问,“生命不是医生的实验品,这个孩子未来数十年生存问题由谁来解决?”也有人认为, “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很棒的,但是,这样却伤害了一个孩子的一生、一个家庭的未来。”还有人干脆说,“谁救活的谁养。医生这样简直是作孽!”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郁琦却表达了对同行的支持。“孩子还没有被确诊,只要有可能残疾,家长就可以决定把他弄死吗?”这位医生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医生做的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
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医生,曾经挽救希腊于瘟疫之中,他同时还是欧洲医学的奠基人。据说,古代西方医生在开业时都要宣读一份有关医务道德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言中的一段这样写着,“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
罗军对媒体说,自己进行了“最为困难、颇多曲折,却有不少奇迹”的“搏斗式抢救”;陈立则认为自己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难熬、痛苦”的夜晚
无论是打人者还是被打者,他们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都觉得自己非常委屈:罗军表示自己在那个凌晨所进行的抢救,是“最为困难、颇多曲折,却有不少奇迹”的“搏斗式抢救”;陈立认为自己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难熬、痛苦”的夜晚。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两年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会议室里,这位中国老人获得了旨在奖励个人和团体在科学伦理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阿维森纳奖”。30年前,他首次将“生命伦理学”引入中国。
“关于新生儿的问题是生命伦理学中讨论最多的,也最难作出判断的。”这位79岁的老人说。
在上个世纪的美国,一个名叫“错误生育”(Wrongful Birth)的案例轰动了医学界和法律界。一对夫妇小心谨慎地对待着还未出生的宝宝,生怕他带有先天畸形。妻子原来分娩过一个死胎,后被证明带有脊髓缺陷和其他方面的畸形。但这次,产科医生信誓旦旦地表示孩子一切正常。
可结果恰恰相反,婴儿一出生就带有先天畸形,在他短短6年的生命里,不断地被大小手术折磨。这对夫妇决定将医生告上法庭,法庭最终裁定被告医生必须为自己的疏忽而担负孩子多年的医疗费用,以及这对夫妇的精神损失费。
尽管法院已经作出了判决,但围绕案子的讨论却持续了很长时间。邱仁宗还记得,各领域的专家最终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一个婴儿出生可能面临着极其低下的生活质量,他必须不断地接受手术,忍受巨大的痛苦,那么父母可以在怀孕期间就选择中止妊娠;若被诊断出胎儿是一个“无脑人”,即无意识,那么父母也可以作出相同的选择。
邱仁宗认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产前诊断,如果发现了问题,家长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尽快流产或者进行产前治疗。
陈立和王静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据王静回忆,就在分娩的十多天前,他们还在医院进行了产检,结果令人安心,胎儿一切正常。
11月3日凌晨,当陈立焦急地等待在手术室外面时,或许还在为“脑瘫儿”或者“大白痴”的未来纠结。这时,护士走出来,告诉他孩子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这位父亲越发坚定了自己的决定:“小孩我不要了,你们不要抢救了,我只要妻子平安。”
可当这个意愿被带回手术室的时候,生命的奇迹已经发生,不久后,护士抱着孩子走出手术室,转往新生儿病房继续治疗。那一刻,他呆住了,“我只能接受现实”。
相比之下,医生罗军是另一种想法:“如果那会儿把孩子的气管拔掉,等于是我杀了这个孩子。”他还反复强调,国家关于放弃新生儿救治的程序非常严格,陈立的情况并不属于放弃救治一类。
但事实上,大夫们常常遇到类似困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医生章伟芳、方曙曾在论文中提到,一个新生儿在出生20分钟后阿氏评分为2分,医生认为无救治价值,但在家长强烈要求下抢救成功。可是6年过去了,这个孩子仍被严重的后遗症影响。
另外一种情况则截然相反。医务人员认为一些缺陷新生儿在积极救治后可达基本的生活能力,但家属要求放弃治疗。
面对“救还是不救”这样的两难选择,章伟芳、方曙认为,不仅要考虑病人的利益,也要考虑他人、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寻找各种利益的最优结合点,在尊重生命神圣的同时捍卫社会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性。
谁也不能决定一个生命是否应该结束,这个叫做伦理
这些学术名词,在陈立和罗军面前却显得很无力。据媒体报道,罗军7岁的女儿问他:“你为什么欺负别人的爸爸?”他的回答是:“爸爸没有欺负他,爸爸是因为救了一个孩子,然后被别人的爸爸欺负。”
而陈立,过去把这个儿子视为希望。如果不是后来被检查出“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话,这个每天都跑儿科病房的“勤快的父亲”可能还会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
邱仁宗认为罗军的做法没错,但如果当晚情况真的如同陈立所描述的那样,说明“医院和病人间的沟通就出现了缺陷”。
“医生向家属讲解病情时,应该有一套标准程序,而这恰恰是中国很多医院所欠缺的。”邱仁宗说。他认为,当医生向陈立讲解病情时,“白痴”二字无疑过于简单化了,也没有考虑到家属的承受能力。当新生儿情况紧急时,“也不可以随便找个护士通知病情,努力抢救是一方面,如何与病人沟通,把信息传达给家属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在美国,残障也曾是件可怕的事。罗斯福曾经拒绝公开他从脊髓灰质炎康复后并不能走远路的事实。肯尼迪总统也隐瞒了自己的皮肤病和其他疾病。可当时间来到2008年,人们在奥巴马的竞选视频中看了一个两岁的孤独症孩子,这位现任美国总统还曾许诺雇用更多残障人士作为联邦雇员。
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时任阿拉斯加州州长的佩林提到了她最小的儿子——特里格,一个唐氏综合症患者。据说,检测得知自己怀的孩子有唐氏综合症的孕妇中90%都会选择堕胎,但佩林没有这样做。
在一次电视节目上,当她被问及是否有“哪怕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想把孩子打掉”的时候,佩林回答说:“当恐惧袭来,面对未卜的前景,一个女人会觉得堕胎是个轻松把问题解决掉的方法,而不去想想,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带着使命降生的。每个小孩都有各自的命运前程,来到我们的世上可以是美好的。”
但即便在美国,这也并不是人们的共识。中国也是如此。陈立和他的孩子的新闻被热议时,一个北京协和医院的女医生表达了对罗军的支持。但她随即遭到了网友的质问,“如果你生了脑瘫儿,你现在就没那么坦然地说平等了”。
这位女医生随后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了这样的回复:“谁也不能决定一个生命是否应该结束。这个,叫做伦理。”
邱仁宗相信,大自然赋予一个人的运气不好,我们无法怪罪大自然。但是,“自然界带来的坏运气,可以通过社会来获得改变。”公平对待、互助组织、社会保障,这些都有可能让先天残障人士及他们的家人生活得更好。
但眼下,陈立和王静仍旧忐忑不安。就在11月21日上午,他们带着孩子再次来到医院进行“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定”,然后兴奋地得知婴儿的评分“及格了”。可为了最终确诊,接下来,他们仍要带着孩子继续接受多项检查和治疗。
这个年轻的母亲还记得,自己第一眼见到儿子时,他的小手四处抓着,用鼻子使劲地呼吸。“我不相信儿子会‘那样’,他很坚强。”王静说。 (文中陈立和王静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何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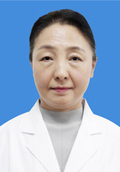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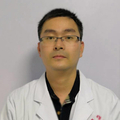 吴泽霖
吴泽霖
 李兰娜
李兰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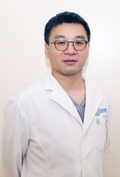


 6岁男童病毒性感冒,之后器官衰竭而亡!只因妈妈给他滥用抗生素2024-06-12
6岁男童病毒性感冒,之后器官衰竭而亡!只因妈妈给他滥用抗生素2024-06-12 新生儿先天性畸形,只因为孕妈孕期做了这四件事,可别再做了2022-11-15
新生儿先天性畸形,只因为孕妈孕期做了这四件事,可别再做了2022-11-15 孕期营养大揭秘!给你吃得好又不胖的孕期!2022-05-27
孕期营养大揭秘!给你吃得好又不胖的孕期!2022-05-27 宝宝呕吐、稀便后突然抽起来?原来这种情况也要防惊厥!2022-04-12
宝宝呕吐、稀便后突然抽起来?原来这种情况也要防惊厥!2022-04-12 @孕妈,产检做妊娠糖耐量试验,攻略看这!2022-04-08
@孕妈,产检做妊娠糖耐量试验,攻略看这!2022-04-08 安顺治抑郁症医院哪家比较好2025-03-28
安顺治抑郁症医院哪家比较好2025-03-28 阜阳治阿尔茨海默病医院哪家比较好2025-03-28
阜阳治阿尔茨海默病医院哪家比较好2025-03-28 阿拉善盟治子宫肌瘤医院哪家比较权威2025-03-28
阿拉善盟治子宫肌瘤医院哪家比较权威2025-03-28 双鸭山治胃溃疡医院哪家比较好2025-03-28
双鸭山治胃溃疡医院哪家比较好2025-03-28 廊坊治疗皮肤过敏的医生2025-03-28
廊坊治疗皮肤过敏的医生2025-03-28
